
文/劉柏君
學生時代的我因為具有陰陽眼的關係,時常要幫鄰里親友解惑。
一開始只是幫忙看看房子、風水,
或是在廟裡幫忙解籤、折符咒,去喪家看看亡人是否還有未交代的遺言?
那時的我只覺得能夠助人很好,可是口耳相傳而來的信徒越來越多,
升上高中時,一些信徒乾脆租了房子、成立一間宮廟,
我每晚十一點開始幫信徒問事服務,直到深夜。
有時候信徒多到要服務到凌晨兩點以後,但是隔天早上六點半,我還是要起床上學。
儘管我真的很想以這個與生俱來的能力幫助大眾,
但是十六歲就要撐起一間宮廟,實在是太沉重了,
才念高中的我被期待能解決千奇百怪的問題,
每天要聽十幾個以上悲苦的人生困境,還有各種病症困擾;
每逢週末還可能要跑中南部甚至國外,這些長期心理上的壓力加上睡眠不足,
我高三開始就深受過度換氣症所苦,甚至在學校昏倒暈厥,多次進出急診室,醫師也只能開類固醇讓我服用。
在宮廟服務期間,我唯一的寄託就是棒球。
除了在學校和同學討論之外,我最期待就是放學後的職棒比賽。
只有在看棒球的時候,我可以完全投入比賽,什麼都不要想;
比賽的那段時間,誰家死人或生小孩?跟誰結婚或想離婚?癌症怪病或墮胎?風水卡陰或被放符?
甚至股票或六合彩明牌,終於不會跟我有關係,我也不必不斷重複問自己:為什麼這都是我的責任?為什麼要期待我解決?
台灣宮廟的生態複雜到難以應付,例如信徒就明明沒有卡陰,但對每個來宮廟求助的都得說有!
都要說後面有跟著不好的髒東西,男的女的或幾個都無所謂,總之必須要祭改、超度才會好。
這不是說謊騙錢嗎?
廟裡人對我說:「大家覺得自己不順、相信妳的能力,妳給他們安慰,他們付點紅包是應該的,這不是說謊騙錢,是各取所需,這叫做生意!」
我開始懷疑賠上青春和健康的自己,到底是在幫人還是害人?
當我陪著喪家去火葬場,陪著信徒去墳場撿骨,
在醫院或告別式上看著那些大體,望著白骨和遺體,我無法停止問自己:這輩子就要這樣過嗎?
雖然這樣賺錢很容易,但是死後是能帶走什麼嗎?
我看過意外而突然離世的大體,也看過小孩的遺體,
棺材裝死不裝老,他們比我還年輕就離開這世界,我怎麼有信心自己還能活多久?
這輩子就要這樣度過嗎?這輩子對我最重要的是什麼?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?
我感覺到生命倒數的壓力,大學畢業之後,我也決定要從宮廟畢業,希望餘下有限的人生能為自己而活。
其實要放棄金錢和信徒的崇拜並不容易,我承認離開宮廟的前幾年,貪念經常作祟,
不過,過去還是太可怕,我很清楚自己不願再走回頭路;
加上有了信仰之後,堅持就沒有這麼痛苦。
在宮廟擔任靈媒的苦,與從棒球中獲得的幸福,兩者的差別清楚且深刻。
所以當友人問我放棄靈媒的工作不眷戀嗎?我總笑答:「不難選啊,球場和墳場,你會選擇去哪一個?」
忍辱拚主審
棒球裁判的分工主要分有「壘審」和「主審」。
壘審就是站在壘包附近,專司安全上壘、出局、界內外球和各種妨礙判決,
主審則是蹲在捕手的後方,除了上述各項判決外,還要加上好壞球的判定。
投手所投出來的每一球都有主審的事情,
想當然所謂的棒球裁判,必須要壘審和主審都擔任過才是完整的棒球裁判。
一般來說,壘審和主審是輪流的,於是我滿心期待能夠擔任主審。
然而,眼看著其他同期的夥伴們站了十場左右的壘審,就開始在強度較低的比賽中站主審執法,
我站了超過一百場壘審,主審的位置還是遙遙無期。
當我覺得自己對壘審的工作游刃有餘後,我開始積極爭取擔任主審,只是沒想到,又是另一段抗爭的過程。
當我多次向前輩反應希望能擔任主審時,可能是被我問得不耐煩了,
他便在眾人面前指著桌上的主審護具說:「劉柏君,我告訴妳為什麼妳不能擔任主審?看到這些主審護具了嗎?這些護具從來都不是為女生設計的,如果妳要站主審,那妳那兩顆ㄋㄟㄋㄟ要放在哪裡?」
我非常憤怒回他:「我會用自己的護具,不是借你的,替我擔心什麼?」
我真的無法理解,為何裁判圈能有這種言論?還說得理所當然、毫無羞恥之心?
除了那次離譜的拒絕,前輩有時也會給我「利誘」安撫,
大意是說,現在能擔任壘審已經很棒了,
主審比較累、比較辛苦,常因為被球打而受傷,何不就好好擔任壘審就好?
好不容易大家已經接納妳當壘審了,不要這樣吵吵鬧鬧想當主審,萬一打壞關係,連壘審都沒得當呢!
可能是累了,想把握擔任壘審的機會,
當時的我接受這樣的說法:「女生能當壘審就很了不起囉!」
我試著告訴自己不要再「吵鬧」,雖然看著其他同期的人站主審還是會羨慕。
還好我安於壘審的念頭沒有太久,
二○○七年底,世界盃棒球錦標賽在台灣舉辦,我擔任澳洲國家隊的翻譯。
當時我和澳洲隊一起到嘉義球場,很不意外的被場務人員吼著:「查某的不要進球員休息區!」
澳洲隊雖然聽不懂中文,但看那場面也大概知道發生什麼事情,
以非常不可思議的口吻問我:「妳不是說棒球是台灣的國球嗎?怎麼會有女生不能進休息區這種事?」
澳洲隊對我非常友善,以前的我根本不敢碰球員的物品,
跟他們在一起時,他們卻借手套和球棒給我一起練習。
球員不但和我玩傳接球,賽前打擊練習時也讓我一起下去玩,甚至教練還餵球給我打擊!
我真的玩得不亦樂乎。有一次,我問澳洲當家捕手:「你會在意主審是女生嗎?」
他說:「我才不管主審是男是女,只要他不要判錯就好。」
教練和球員都鼓勵我要站主審,甚至投捕練習時,就讓我蹲後面做判決,每次拉三振時,全場都是大家滿滿的笑聲。
他們鼓勵我一定要力爭擔任主審,我遲疑的表示大家都說我辦不到,
球員卻說:「愛妳的人會希望妳快樂、做妳想做的事情,不愛妳的人則希望妳做不到。妳要聽愛妳的人說的話?還是不愛妳的人說的話?」
當然是要聽愛我的人說的話啊!
球員說:「是啊,我們相信妳做得到,妳應該去爭取。我上過大聯盟投球,我投的球妳都能判了,其他的怎麼可能不能判?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。別怕,我就站在妳身後。」
結束那三個星期的翻譯工作後,我決定要力爭主審執法的機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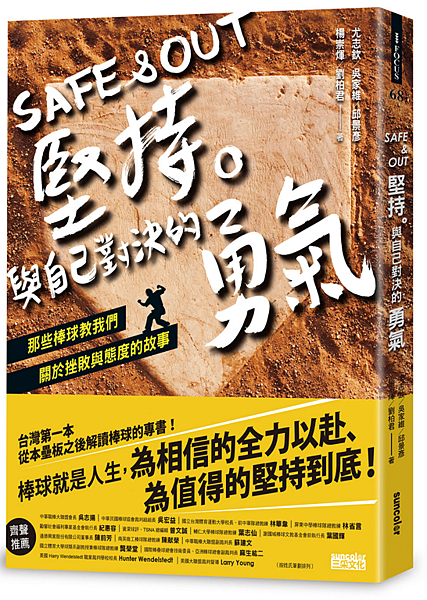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